【四】
“人”是怎麼來的呢?“人”又是怎樣一種存在?
據說,有一次,“操心”[Cura]女神渡河之際,看到一片膠泥,她若有所思地玩起了泥塑,終於用泥土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朱庇特給了“人”以靈魂,土地神(臺魯斯)貢獻了泥坯,他們都爭著要給“人”命名,農神(時間)裁判說:朱庇特在人死後得到人的靈魂,土地神在人死後得到人的身軀(泥坯),“操心”則佔有人的“活著”。至於大家都爭論的名稱就叫“homo”(人)吧,因為它是由humus(泥土)造的。[P228]
塞涅卡在其《使徒書》中寫道:“在四類生存的的自然(樹、獸、人、神)中,唯有後兩類賦有理性,而後兩類的區別則在於神不死而人有死。於是在這兩類中,其一即神的善由其本性完成,而另一即人的善則由操心完成。”[P230]
生存論結構,此在的本質即是被拋世界操心籌劃可能性存在。人能夠為他最本己的諸種可能性而自由存在,而在這種自由存在(籌劃)之際成為他所能是的東西,這就叫人的“完善”。
這裡所提到概念不是存在者現成事物意義上的概念,這裡的“普遍化”是一种先天存在論的普遍化。“操心”的優先地位在於它把人看成軀體(泥坯)和精神的複合體。寓言表達出了對人的本質的先於存在論的規定。在“操心”這種存在方式中,存在建構的“先天性”“早于”此在的一切設定和行止。
傳統文化所信仰的“外部世界”的實在性、主體與客體的設置,屬於在世的“衍生物”,實在論(唯物論)、經驗論、和唯心論(唯我論)、理性論等解決“實在問題”的嘗試,迷失了道路,耽擱了此在生存論分析。
唯心論比唯物論優越,如果唯心論強調的是存在和實在只在“意識之中”,那麼這裡就表達出了一種領會,即存在不能由存在者來解釋。如果唯心論意味著把一切存在者都引回到主體或意識,而主體與意識就它們的存在來說始終表現為無所規定的,或最多只被消極地標畫為“非物質的”,那麼,唯心論與實在論同樣幼稚。可見,歷史上關於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爭論往往是各持己見、失于片面,甚而變異為意識形態的爭鬥。
狄爾泰指出,實在的東西在衝動和意志中被經驗到,實在性是阻力,是阻礙狀態。[P241]舍勒指出,認識本身也不是判斷活動,知乃是一種“存在關係”。[P242]慾望和意志乃是操心的變式,此在若不生存,“實在”、“自在”、“獨立性”也就不“在”,沒有此在之領會,沒有對存在可能性之領會,就沒“有”存在,人的實質是“生存”,存在的本質就是“有所給予”。於此,筆者不敢茍同,存在到底是給予還是匱乏的問題有待考察。
巴門尼德首次揭示了存在者的存在,把存在同聽取著存在的領會“同一”起來。亞裏士多德強調說,在他之前的哲人是由“事情本身”所引導而不得不進行追問,即他們為“真理”的所迫而進行研究。哲學被標為關於“真理”的科學,考察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科學。
考察傳統“真理”:(1)真理的“處所”是命題(判斷)。(2)真理的本質在於判斷同它的對象相“符合”。(3)亞裏士多德這位邏輯之父既把判斷認作真理的源始處所,又率先把真理定義為“符合”。亞裏士多德說:靈魂的“體驗”,“表像”,是物的肖似。[P247]這是“知與物的肖似”。康得認為,“真理或假像並不在被直觀的對象裏面,而是在被思維的對象的判斷裏面。” [P248] 把“真理”標畫為“符合”是十分普遍而又空洞的。
一個命題是真的,這就意味著:它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它在存在者的被揭示狀態中說出存在者、展示存在者、“讓人看見”存在者。命題的“真在”(真理)必須被理解為揭示著的存在。[P251]真在這種進行揭示的存在是此在的一種存在方式。揭示活動本身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首先指出了最源始的真理現象。揭示活動是在世的一種方式,尋視著的操勞或甚至逗留著觀望的操勞都揭示著世內存在者。[P253]
世內存在者的揭示狀態奠基於世界的展開狀態。展開狀態是此在的基本方式。展開狀態是由現身、領會和話語來規定的。操心結構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經在一世界中的——作為寓於世內存在者的存在。操心的這種結構包含著此在的展開狀態于自身。只要此在作為展開的此在開展著、揭示著、那麼,它本質上就是“真的”。此在“在真理中”。這一命題具有存在論意義。[P254]
“此在在真理中”這一原理的生存論意義需要如下諸項規定:(1)、此在的生存論結構從本質上包含有一般展開狀態。(2)、此在的存在建構包含有被拋境況;被拋境況是此在的展開狀態的構成環節。(3)、此在的存在建構包含有籌劃,即向此在的能在開展的存在。(4)、此在的存在建構包含有沉淪。[P255]
真理(揭示狀態)總是要從存在者那裏爭而後得。存在者從晦蔽狀態上被揪出來。實際的揭示狀態總仿佛是一種劫奪。希臘人在就真理的本質道出他們自己時,用的是一個剝奪性質的詞[去蔽],並非偶然。[P256]
“說、邏各斯”這種“讓人看”的“是真”乃是一種“揭示”方式的“真在”:把存在者從晦蔽狀態取出來而讓人在其無蔽(揭示狀態)中來看。此在“在真理中”、“全真境界”;“此在在不真中”。存在之遮蔽與敞開、揭示與封閉、假像與偽裝、沉淪與遺忘,真理通過“去蔽”而顯現,真理實際上像是一種“劫奪”,消散於人之中是常人的存在方式。真理是與此在相聯繫的,“真理”不是主觀的,真理與此在必須存在。
【五】
哲學的課題是“先天性”,而不是“經驗事實”本身。“理想主體”是一個用幻想加以理想化的主體,與“事實上的”主體的先天性,亦即此在的先天性,失之交臂。此在之可能的整體向死而生。從時間性方面就能理解到為什麼此在基於它的存在就是歷史性的和能是歷史性的,並且能作為歷史性的此在營造歷史學。此在在世操心時間,此在的時間性造就了“計時”,不完整性意味著在能在那裏的虧欠,此在從不曾達到它的“整全”。死亡就是此在不在世,此在這種存在者的終結就是現成事物這種存在者的端始。
此在身上持續“不完整性”(“虧欠”),並且以死亡告終。我們把齊全與基於齊全的不齊全標畫為“總額”(整體、總數)。“剛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波希米亞的耕夫》)[P282]此在(尚未、存在、結束、整體性)死亡的生存論闡釋先於一切生物學和生命存在論,而且它也才奠定了一切對死亡的傳記——歷史的研究的和人種——心理研究的基石。
生存論問題的提法唯以整理出此在向終結存在的存在論結構為標的。死亡,此在之能在不可逾越之可能性,此在之最本己“懸臨”,向死而生。此在、在世、操勞、畏(死)、沉淪、逃避,這些語詞勾勒出此在的生存的一面。此在之存在的諸種基礎性質:在先行于自身中,生存;在已經在某某之中的存在中,實際性;在寓于某某的存在中,沉淪,由此標畫著向終結存在的特徵。誘惑、安定與異化卻標識著沉淪的存在方式。日常的向死存在作為沉淪著的存在乃是在死面前的一種持續的逃遁。在生存論的標畫中,向終結存在在被規定為向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不可逾越的能在存在。死確定會到來,但尚未。死隨時隨刻都是可能的。死既確定又不確定。日常操勞活動為自己把確知的死亡的不確定性確定下來的方法是:它把切近日常的放眼可見的諸種緊迫性與可能性堆到死亡的不確定性前面來。這裡談的是生存論存在論的死亡概念。[P297]
向死存在本質上就是畏,此在向死存在中領會(有限性、極端、終結)無可逾越之境而給自身以自由。去存在之極端可能性懸臨。此在先行著,防護自身以免於回落到自己本身之後以及所領會的能在之後,並防護自身以免於“為它的勝利而變得太老”(尼采)。對從生存論上所籌劃的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特徵標畫可以概括如下:先行向此在揭露出喪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況,並把此在帶到主要不依靠操勞操持而是去作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這個自己卻就是在熱情的、解脫了常人的幻想的、實際的,確知它自己而又畏著的向死的自由之中。[P306]
隨著喪失于常人之中的境況,此在的切近的實際能在——諸種任務、規則、措施、操勞在世和操持在世的緊迫性與廣度——總已被決定好了。常人悄悄卸除了“選擇”可能性的責任。
此在“耽擱”于非本真狀態,卻又不得不“補做選擇”,聽從良知的聲音的呼喚、召喚,選擇即是決心。此在現身領會話語,沉淪中的常人聽,卻充耳不聞良知的呼喚。若說迷失了的聽沉迷于日常“新奇”閒言中各式各樣模棱兩可的“嘈雜”,那這呼聲必定以不嘈不雜、明白單義、無害好奇立足的方式呼喚著。以這種方式呼喚著而令人有所領會的東西即是良知。[P311]
良知——呼聲——法庭(康得術語)。呼聲由遠及遠,唯欲回歸者聞之。我們所稱的良知,即呼喚,是在其自身中召喚常人自身;作為這樣一種召喚,它就是喚起這個自身到它的能自身存在上去,因而也就是把此在喚上前來,喚到它的諸種可能性上去。[P314]此在被召喚向本己的自身,呼聲不付諸任何音聲,良知只在而且總在沉默的樣式中言談,使此在進入本己的緘默。良知從喪失于常人的境況中喚起此在本身。呼聲出於我而又逾越我又來到我這裡。此在作為被拋的此在被拋入生存。它作為這樣一種存在者生存著:這種存在者不得不如它所是的和所能是的那樣存在。[P316]
此在躲避被拋境況,逃到“常人”中求輕鬆,這一逃遁被標識為無家可歸的狀態,它其實規定著個別化的在世。無家可歸在畏的基本現身情態中本身地暴露出來:它作為被拋的此在的最基本的展開狀態把此在在世擺到世界之無面前,而此在就在這無面前,在為其最本己的能在的畏中生畏。[P317]
此在在世界之無中的赤身裸體的“它存在”。良知將此在喚回到生存能在的緘默之中。如果不是由於此在在委棄自身之際而煢煢孑立,還有什麼能這樣決絕地剝奪了此在從其他途徑來誤解自己和誤認自己的可能性呢?[P317]
無家可歸狀態追迫著此在,使它忘卻自身的迷失狀態受到威脅。良知公開自身為操心的呼聲,良知的呼聲,即良知本身,在存在論上之所以可能,就在於此在在其存在的根基處是操心。[P318]
所謂“公共良知”、“世界良知”(上帝、道德)乃是“常人”的聲音,而“良知向來是我的良知”,這不僅意味被召喚的向來是最本己的能在,而且也因為呼聲來自我向來自身所是的那一存在者。[P319]“良知”的呼聲這樣那樣,無非在說“罪責”。[P320]有罪責並非作為某種欠債的結果的出現,相反,欠債只有 “根據于”一種源始的有罪責才成為可能。[P 325]
操心本身自始至終貫穿著“不之狀態”,此在之為此在就是有罪責的——茍若從生存論上講確乎可以從形式上把罪責規定為不之狀態的根據性存在。此在、操心、沉淪、被拋、良知、罪責、本真狀態,這些術語的勾連似乎標識著此在如何從沉淪中返回到它自身最本己的能在,即本真狀態。此在的有罪責不同於道德意義上的欠債或有責,源於此在之被拋的操心的“不性”,良知召喚此在之沉淪回歸於本真存在,解除罪責之罰。這種緘默的時刻準備畏的、向著最本己的罪責存在的自身籌劃,我們稱之為決心。[P339]
處境(形勢)——“處其勢而能作某事”這一術語帶有空間含義。處境只有通過決心並在決心之中才存在。處境本質上對常人封閉著,常人只識得“一般形勢”,喪失了切近的“機會”,靠總計“偶然事件”維持此在。[P342]
從存在論著眼,此在原則上有別於一切現成事物與實在事物。此在的“實在”並非根據某種實體的實在性,而是根據于去存在的自身的“獨立自駐”。我們曾把這一自身的存在理解為操心。[P346]
源始的從現象上看,時間性是此在的本真整體存在那裏、在先行著的決心那裏被經驗到的。[P347]此在的一切基礎結構,就它們可能的整體性統一和鋪展來看,歸根到底都須被理解為“時間性的”,理解為時間性到(其)時(機)的諸樣式。[P347]
決心等於說:讓自己被喚向前去,喚向最本己的罪責存在。罪責存在屬於此在本身的存在;而我們曾把此在的存在首要地規定為能在。“有罪責”只在當下實際的能在中存在。[P349]對良知呼聲的領會展露出失落到常人中的境況。決心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存在。在有所領會地向死這種最本己的可能性存在之際,本己的能在就成為本真的和通體透徹的。[P350]
【六】
知性無論是“理論的”還是“實踐的”都只操勞于可由巡視周覽的存在者。知性的別具一格之處在於它只意在經驗“事實上的”存在者,以便能擺脫對存在的領會。它忽視了:即使還不曾從概念上把握了存在,但只有已領會了存在,才能“從事實上”經驗到存在者。知性誤解了領會和領會的性質。[P360]
表達操心結構的生存論公式:先行于自身的——已經在(世界中的)——作為寓于(世內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P361]先行于自身表現為尚未,本然生存在“虧欠”的意義上標識為先行于自身,先行于自身便綻露為向終結存在。操心在良知呼聲中向最本己的能在喚起此在。[P361]
“我”是邏輯行為的主體,是維繫的主體。“我思”等於說“我維繫”。[P364]在說我之際此在把自己作為在世的存在說出。此在因沉淪而逃避它自己,逃到常人中去。常人自身我呀我呀說得最響最頻,因為它其實不本真地是它自身並閃避其本身能在。[P367]獨立性或常駐于自身的狀態就是針對無決心的沉淪的無獨立性或常駐于非自身狀態這一情形的本真的反可能性。獨立自駐在生存論上恰就意味著先行的決心。[P367]
我們把此在的存在整體性規定為操心。意義就是某某事物的可理解性持守于其中之處,而同時這某某事物本身卻並不明確地專題地映入眼簾。意義意味著首先的籌劃之何所向,從這何所向方面,某某事物作為它所是的東西能在其可能性中得以把握。籌劃活動開展出種種可能性即開展出使事物成為可能的東西來。[P369]
當我們說,存在者“有意義”,那麼這意味著,它就其存在得以通達了;存在是存在者向之得以籌劃的何所向,所以,存在才“本真地”“有意義”。存在者“有”意義,只因為存在已經事先展開了,從而存在者在存在的籌劃中成為可以領會的,亦即從這一籌劃的何所向方面成為可以領會的。存在之領會的首要籌劃“給出”意義。[P370]尼采曾說,真理就像一位女子,需要我們的追求。
生存的源始的生存論籌劃所籌劃的東西綻露為先行的決心。此在的向死存在的先行使此在本真地是將來的。只有當此在如“我是所曾在”那樣存在,此在才能以回來的方式從將來來到自己本身。此在本真地從將來而是曾在。先行達乎最極端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有所領會地回到最本己的曾在來。只有當此在是將來的,它才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種方式源自將來。[P371]
我們把如此這般作為曾在著的有所當前化的將來而統一起來的現象稱作時間性。只有當此在被規定為時間性它才為它本身使先行決心的已經標明的本真的能整體存在成為可能。時間性綻露為本真的操心的意義。[P372]操心的結構的源始統一在於時間性。生存論建構的首要意義就是將來。[P373]實際性首要的生存論意義即在於曾在。生命時間的“河流”。筆者保留,時間何以取得先於空間的優越地位。
下了決心的此在恰恰是從沉淪中抽回身來了,以求“當下即是地”愈加本真地朝向展開的處境在“此”。[P374]將來、曾在與當前顯示出“向自身”、“回到”、“讓照面”的現象性質。[P374]時間性是源始的、自在自為的“出離自身”本身。將來、曾在、當前等現象稱為時間性的綻出。時間性的本質即是在諸種綻出的統一中到時。時間性並非先是一存在者,而後才從自身中走出來。流俗所領會通達的“時間”的種種特性之一恰恰就在於:時間被當作了一種純粹的、無始無終的現在序列。如此則源始時間性的綻出性質被“敉平”了。源始而本真的時間性的首要現象是將來。[P375]
時間源始地作為時間性的到時存在;作為這種到時,時間使操心的結構之建製成為可能。時間性在本質上是綻出的。時間性源始地從將來到時。源始的時間是有終的。[P377]此在首先與通常處身於其中的那種通常的存在方式稱為日常狀態。此在持駐于自身的狀態[獨立性]與持駐于非自身的狀態[不獨立性],時間性綻露為此在的歷史性。此在出現在一種“世界歷史”之中。此在為它自身運用它自己,巡視的操勞,此在“用損”它自己。由於“用損”自己,此在需用它自己本身,亦即需要時間,存在估算時間。我們把世內存在者的時間規定性稱為時間內性質或時間內狀態。[P379]
“存在之時間”發源於源始時間性的一種到時方式。現成事物“在其中”生滅的時間是一種真切的時間現象,而不似柏格森的時間解釋——要讓我們相信的那樣,仿佛那種時間是“具有質的時間”外在化為空洞的結果。[P380]只有把此在的時間性整理為日常性、歷史性和時間內性質,我們才能無所顧及地洞見源始的此在存在論的盤根錯節之處。[P380]筆者質疑就時間論時間的性質。
【七】
沉淪著的有情緒的領會就其可理解性而在話語中勾連自己。只有在個別化中此在才把自己帶向其最本己的能在,而就這種最本己的能在來說,首先與通常此在是被封閉了的。……時間性並不常駐地從本真的將來到時。……將來的到時是會發生衍變的。[P383]
預期是將來的一種植根在期備中的樣式;而將來則本真地作為先行到時,從而與在操勞活動中對死的預期相比,在先行中有一種更加源始的向死存在。[P384]我們把保持在本真的時間中的並因而是本真的當前稱為“當下即是”。必須在積極的或動態的意義上把這一術語領會為一種綻出樣式。[P385]我們把非本真的當前稱為“當前化”,以與本真的當前即是相區別。……當前化總是意指非本真的、不是當下即是的、無決心的當前。[P386]
遺忘並非無或只是記憶的闕失,遺忘曾在狀態固有的一種“積極的”綻出樣式。遺忘這種綻出(放浪)具有如下性質:封閉著自己本身而在最本己的曾在面前放溜。[P386]正如預期只有基於期備才是可能的,記憶也只有基於遺忘才是可能的,而不是相反。[P386]
情緒以趨就或背離本己此在的方式開展著。唯當此在的存在按其意義來說是持駐地曾在,才可能在生存論上 [把此在]帶到“它存在且不得不存在”這一本己的被拋境況面前,不管這一被拋境況是本真地有所綻露還是非本真地有所遮蓋。[P387]
情緒被當作流變的體驗,這些體驗為“靈魂狀態”的整體“謀上色彩”。[P388]怕曾被描述為非本真的現身情態。怕是在某種具有威脅性質的東西面前害怕。怕的生存論時間性意義由一種自身遺忘組建起來;這種自身遺忘是:在本己的實際能在面前迷亂放溜,而被威脅的在世就作為這種迷亂放溜而操勞于上手事物。……抑制把此在逼回到它的被拋境況,而其方式卻恰恰是使被拋境況封閉起來。迷亂奠基於一種遺忘。在實際的下了決心的能在之前遺忘著放溜,這種活動附於先前就由巡視揭示開來的諸種自救與閃避的可能性,懼怕著的操勞活動因為遺忘自己並從而不掌握任何“可能的”可能性,亦即連不可能的可能性也包括在內,紛陳眼前。害怕的人不把定任何一個;“周圍世界”並不消失,而是在不復在周圍世界之中認出自己的境況下來照面。[P389]
我們曾把畏這種現象稱為一種基本現身情態。它把此在帶到其最本己的被拋存在之前,並綻露出日常所熟悉的在世的無家可歸性質。[P390]周圍世界的存在者斷了因緣。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向著無意蘊沉降、而借此被展開的世界則只能開放出以無因無緣為性的存在者。
畏之所畏為世界之無;而世界之無不等於說:在畏中似乎經驗不到世內現成事物的某種不在場。恰恰是世界現成事物必須來照面,這樣一來它便蕩然全無因緣而會在一種空蕩蕩無所慈悲的境界中顯現。[P391]被拋入無家可歸狀態的此在是赤裸裸的此在,畏就因這赤裸裸的此在而畏,畏(把此在)帶回到純粹的“它存在且不得不存在”,帶回到最本己的、個別化的被拋境況。[P391]
對怕起組建作用的遺忘迷性亂真而讓此在在未經掌握的“世界的”可能性之間衝來蕩去。與這種未經把持的擺到當前相對的是在把自己帶回到最本己的被拋境況中的對畏之當前的把持。……畏只是帶入某種可能作決定的情緒,畏之當前本身就是作為“當下即是”存在並且只有它可能作為當下即是存在;它以正在躍起的方式把持住這一當下即是。[P391]筆者質疑畏高於怕的生存論意義,不無牽強之處。
怕從世內事物襲來。畏從被拋向死存在這一在世升起。[P392]畏發源於決心的將來;而怕發源於失落了的當前,怕因會懼怕而怕當前,結果恰恰就這樣沉淪到失落了的當前。[P392]怕關係到一種[將來的惡事],而希望的特點則是對一種[將來的好事]的預期。決定現象結構關鍵卻不是希望與之發生關係的東西的“將來”性質,而是希望這種活動自身的生存論意義。[P393]
沉著這種情緒發源於決心,而決心當下即是直面先行到死所展開的整體能在所可能具有的諸種境況。[P393]好奇完完全全以非本真的方式而是將來的……好奇是由一種難以居持的當前化組建的,這種當前化只顧當前化,從而不斷設法從它難以居持地“居持”在其中的期備脫身。好奇以這樣“跑開”的意義上的期備“跳開”方式當前化,卻不是投身於“事”,它倒是在看到一眼之際就已向一最新近的東西轉盼了。……渙散……當前化通過跟著跳的期備而愈發委棄于它自身……自己拘囚于自身,渙散的無所延留成為無所去留。這種當前樣式是“當下即是”的最極端的反現象。在這種無所去留的當前中,此在到處在而又無一處在。而當下即是則把生存帶入處境並開展著本真的“此”。[P396]
好奇總已經去抓下一個而遺忘了上一個。沉淪的諸種性質:欲求、安定、異化和自我拘囚。領會首要地奠基於將來(先行與期備)。現身情態首要地在曾在狀態(重演與遺忘)中到時。沉淪在時間性上首要地植根于當前(當前化與當下即是)。然而領會也是向來“曾在”的當前,現身情態也作為“當前化的”將來到時;當前也從一種曾在的將來“發源”和“跳開”,並且由曾在的將來所保持。在這裡可以看到:時間性在每一種綻出樣式中都整體地到時,即:生存、實際性與沉淪的結構整體的整體性,也就是說,操心之結構的統一,曾奠基於時間性當下完整到時的綻出統一性。[P398]
到時不意味著諸綻出樣式的“前後相隨”。將來並不晚于曾在狀態,而曾在狀態並不早于當前,時間性作為曾在的當前化的將來到時。[P398]此在這一存在者是“明敞的”,使它為自身“敞開”而又“明亮”的東西先於一切“時間性的”闡釋曾被規定為操心,在操心中奠定了此的整個展開狀態。這一明敞才使得一切光明和照明成為可能,才使得一切知覺某事、“看”某事與有某事成為可能。[P399]
綻出的時間性源始地敞明“此”。此在在世在周圍世界中與周圍世界打交道……某種東西同某種東西結因緣,這話不應是從存在者層次上確認一件事實,而是提示著上手事物的存在方式……操勞以尋視方式有所揭示地寓于……而存在,這種存在是一種了卻因緣,亦即有所領會地對因緣作籌劃。如果了卻因緣成了操勞的生存論結構而操勞作為寓于……的存在屬於操心的本質建構,如果操心卻又奠基在時間性中,那麼就必須在時間性的某種到時樣式中尋找了卻因緣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論條件。 [P402]
其實,在我們遭遇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分析的時候,我們慣見了他的“鉤鐮槍法”,海德格爾用他特有的語匯通過現象學還原加上闡釋學的展開再加上他精心地語詞勾連,於是“人”的此在狀態似乎就被心理學式的分析了出來。這裡可以看見他有些詩意化了的哲學道路。在此,劍門若郎也以“鉤鐮槍法”引用海德格爾的大段文字及其語匯嚴密而又跳躍地“相互勾連”來接近和解讀海德格爾詩意化了的哲學。讀者無怪。
【八】
為了能“失落于”用具世界,為了能“現實地”去工作去操作,自身必須遺忘自己。……我們從生存論上把了卻因緣領會為讓“存在”。基於這種讓“存在”,上手事物作為它所是的存在者向尋視照面。所以,如果我們注意尋視著“讓照面”的諸種樣式,即我們先前描述為觸目、窘迫與膩味的那些樣式,我們還能進一步廓清操勞的時間性。[P403]
若有所失絕不是不當前化,而是當前的一種殘缺樣式,其意義是:把某種預期和某種總已可資利用的東西的不當前擺到當前。……失落了的當前化未作期待,這才開展出“視野上的”餘地,使令人吃驚之事能襲擊此在。[P404]
即使操勞活動限于日常必需的緊迫之事,它也仍然從來不是一種純粹的當前化,而是從一種有所期備的居持中發源的,而此在就根據于這一有所期備的居持並作為這一居持的根據而生存在一個世界中。所以實際生存的此在即使在一個陌生的“世界”中也總已經以某種方式認出它自己。[P405]
“邏輯上的”概念與科學的生存論概唸有別,它從科學的結果來著眼來領會科學並把它規定為“真命題,亦即有效命題組成的論證聯繫”。生存論概念把科學領會為一種生存方式,並從而是一種在世方式:對存在者與存在進行揭示和開展的一種在世方式。然而,只有從生存的時間性上澄清了存在的意義以及存在與真理之間的“聯繫”,才能充分地從生存論上闡釋科學。[P406]
對存在者的純觀看是由於操勞從當下操作抽身而發生的。作為“係詞”的“是”所“表達”的就是把某種東西作為某種東西來說。科學形成的關鍵不在於給予對“事實”的觀察以更高的估價,也不在於把數學“應用”來規定自然進程,而在於對自然本身的數學籌劃。……數學籌劃對先天的東西有所開展。[P411] ……它們能把自己向著純揭示活動“對拋”,亦即成為“對象”或“客體”。
如果“主體”在存在論上被理解為生存著的此在而其存在奠基在時間性中,那麼必須說:世界是“主觀的”,但這個“主觀的”世界作為時間性的超越的世界就比一切可能的“客體”更“客觀”。[P415]
此在從不、甚至[在日常狀態上]也從不首先現成存在在空間中。……此在設置空間……此在生存著向來就佔得了一個活動空間……它從設置了的取得了的空間回到它訂好了的“位置上”。[P417]
因為此在是“精神性的”,並且只因為這個,此在具有空間性的方式才可能是廣延物體本質上始終不可能具有的方式。[P417]只有根據綻出視野的時間性,此在才可能闖入空間。世界不現成存在在空間中,空間卻只有在一個世界中才得以揭示。[P419]
在此在的存在中已經有著與出生和死亡相關的“之間”。絕非是相反的情況,仿佛此在在某一時間點上現實地“存在”,而此外還被它的出生和死亡的不現實“圍繞”著。……只要此在實際生存著,兩個“終端”及它們的“之間”就存在著……作為操心,此在就是“之間”。[P424]
生存的行運不是現成事物的運動。……是從此在伸展著的途程得以規定的……此在的演歷。[P425]此在歷史性的分析想要顯示的是這一存在者並非因為“處在歷史中”而是“時間性的”,相反,只因為它在存在的根據處是時間性的,所以它才歷史性地生存著並能夠歷史性地生存。[P427]
歷史之為過去之事總是就其對“當前”的積極的或闕失的效用關聯得以領會的,而“當前”的意義則是“在現在”和“在今天”現實的東西。[P428]歷史意味著一種貫穿“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事件聯繫和“作用聯繫”。……歷史還意味著“在時間中”演變的存在者整體。……歷史意味著人的、人的組合及其“文化”的演變和天命,……人們著眼於人的生存的本質規定性,即通過“精神”和“文化”把這一存在者的領域與自然區別開來,雖說如果這樣領會歷史,即使自然也以某種方式屬於歷史。[P429]
概括之,歷史是生存著的此在所特有的發生在時間中的演歷;在格外強調的意義上被當作歷史的則是:在共處中“過去了的”而卻又“流傳下來的”和繼續起作用的演歷。[P429]
首要地具有歷史性的是此在。而世內照面的東西則是次級具有歷史性的;這不僅包括最廣泛意義下的上手用具,而且包括作為“歷史土壤”的自然的周圍世界。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由於屬於世界而具有歷史性;我們稱這類存在者為世界歷史事物。可以顯示:流俗的“世界歷史”概念的源頭恰恰在於依循這種次級的歷史事物制訂方向。世界歷史事物並非由於歷史學的客觀化而具有歷史性;而是,它作為那以世內照面的方式是其自身所是的存在者而具有歷史性。[P432]
劍門若郎始終懷疑海德格爾的此在時間性及其歷史性的論斷,特別是其時間性作為此在的本質以及時間被看著空間的真理意義。不能信服。
【九】
我們用命運來標識此在在本真決心中的源始演歷;此在在這種源始演歷中自由地面對死,而且借一種繼承下來的、然而又是選擇出來的可能性把自己承傳給自己。[P434]
只有這樣一種存在者,它就其存在來說本質上是將來的,因而能夠自由地面對死而讓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拋回其實際的此之上,亦即,作為將來的存在者就同樣源始地是曾在的,只有這樣一種存在者能夠在把繼承下來的可能性承傳給自己本身之際承擔起本己的被拋境況並當下即是就為“它的時代”存在。只有那同時既是有終的又是本真的時間性才使命運這樣的東西成為可能,亦即,使本真的歷史性成為可能。[P436]
本真的向死存在,亦即時間性的有終性,是此在歷史性的隱蔽的根據。[P437]在決心中有先行著把自己承傳于當下即是的“此”這回事,這一傳承我們成為命運。天命就奠基於其中——我們把天命領會為此在共他人存在之際的演歷。[P437]
此在作為有時間性的此在是以綻出方式敞開的。如果歷史性屬於此在的存在,那麼非本真的存在也不能不是有歷史性的。[P438]歷史實際上既非客體變遷的運動聯繫也非“主體”的漂浮無據的體驗的持續。……歷史的演歷是在世的演歷,……上手事物與現成事物向來已隨著歷史性的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被收入世界的歷史。[P439]
我們選擇的“世界歷史”這個詞在這裡是從存在論上來領會的,於是須得注意它的雙重含義:一方面它就世界與此在的本質上的生存上的統一而意味世界的演歷。但就世內存在者向來已隨實際生存上的世界得到指示而言,“世界歷史”同時就意指上手事物與現成事物在世內的“演歷”。[P439]
此在在其自身的何種存在方式中迷失得如此之甚,而結果竟仿佛不得不只在事後才從渙散中攏集自己,不得不為了攏集而為自己發明出一種包羅無遺的統一?[P441]決心組建著對向著本真自身的生存的忠誠。作為準備去畏的決心,忠誠同時又是對自由生存活動所能具有的唯一權威的可能敬畏,是對生存可重演的諸種可能性的敬畏。[P442]
此在作為常人自身不持立地把它的“今天”當前化。此在一再期待著切近的新東西,一面也已經忘卻了舊的。常人閃避選擇;常人盲目不見種種可能性;它不能重演曾在之事,而只不過保持和接受曾在的世界歷史事物余留下來的“現實之事”,以及殘渣碎屑與關於這些東西的現成報導。常人迷失于使今天當前化的活動,於是它從“當前”來領會“過去”。本真歷史性的時間性則反過來作為先行而有所重演的當下即是剝奪今天的當前性質和常人的約定俗成。非本真地具有歷史的生存則相反,它背負著對其自身來說已成為不可認識的“過去的”遺物,去尋求攀登的東西。本真的歷史性把歷史領會為可能之事的“重返”;而且知道:只有當生存在下了決心的重演中命運使然地當下即是可能性敞開,這種可能性才重返。[P442]
歷史學對“過去”的開展奠定在命運使然的重演中,這種開展不是“主觀的”,反倒只有這種開展保障了歷史學的“客觀性”。因為一門科學的客觀性首要地取決於它是否能把包含在它課題中的存在者無所掩蔽地在其存在的源始性中迎面帶向領會。常人及其知性都要求尺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聲稱“普遍性”,而這些東西在本真的歷史學中比在任何科學中都更不是“真理”的可能標準。[P446]
一個歷史學家可以一下子就“投身於”某個時代的“世界觀”,但卻並不由此證明他本真地從歷史上而非僅僅從“美學上”領會他的對象。另一方面,一個人“僅僅”輯訂資料的歷史學家的生存卻可能是由一種本真歷史性規定的。[P447]
尼采區分了三種歷史學:紀念碑式的、尚古的與批判的歷史學。[P447]歷史真理的可能性與結構要從歷史生存的本真展開狀態(“真理”)得到演示。[P448]
“整個心理物理的給定狀態並非存在著(存在=自然的現成存在,作者注),而是生活著,這是歷史的萌發點。對自身的思考並不指向一個抽象的我而是指向我自身的全幅;這種思考發現我是從歷史學上規定的,正如物理學認識到我是從宇宙學論上規定的。我是歷史,一如我是自然的。”約克看透了一切不真實的“關係規定”和“無根基”的相對主義;他毫不躊躇地從對此在的歷史性的洞見中抽出最後的結論:“然而另一方面,就自我意識的內在歷史性說,一種從歷史中離異出來的體系在方法論上是不充分的。正像心理學不能從物理學上抽離開一樣,哲學,尤其當它是批判的時候,也不能從歷史性抽離出來……自身的行為與歷史性就像呼吸與氣壓一樣,而且,即使聽起來有幾分悖謬,但從方法的聯繫上來說,哲學運動的非歷史化在我看來卻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殘余。” [P454]
約克自己已經反對著存在者層次上的東西(視覺上的東西)而走上了從範疇上把歷史學上的東西收入掌握的道路,走上了把“生命”上升到適當的科學領會的道路。[P454]
“悖論是真理的一項標誌。在真理中斷然沒有[公論],那只是進行一般化的一知半解的沉積、元素式的沉積,它對於真理的關係就好像是閃電過後留下的硫磺霧。真理從不是元素。政治教育的任務似乎是去消解元素式的公眾意見,是盡可能使看待事物的個體眼光得以建立。於是,個體的良知,亦即良知,將取代所謂的公眾良知這種極端的外在化,而重又變得強勁。”[P455]
【十】
在流俗時間概念的成形過程中顯現出一種引人注目的遊移:究竟應得把“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性質歸屬於時間呢?把它看作是自在存在著吧,它卻又顯著地歸於“心靈”;說它具有“意識”性質吧,然而卻又“客觀地”起作用。在黑格爾對時間的闡釋中,這兩種可能性得到某種揚棄。黑格爾試圖規定“時間”與“精神”之間的聯繫,以便借此弄明白為什麼精神作為歷史“落在時間之中”。[P458]
因為時間性以綻出視野組建著此的明敞,所以它源始地在此之中總已經是可解釋的並從而是熟知的。我們把解釋著自己的當前化亦即那作為“現在”而談及的被解釋的東西稱為“時間”。[P461]
實際被拋的此在之所以能夠“獲得”或喪失時間,反只在於它作為綻出的、伸展了的時間性又被賦予了某種“時間”,而這種賦予是隨著植根于這種時間中的此在的展開而進行的。[P464]
操勞活動利用放送著光和熱的太陽的“上手存在”,太陽使操勞活動中得到解釋性的時間定期。從這一定期中生長出“最自然的”時間尺度——日。[P466]隨著那被拋的、遺托給“世界”的、給與自己時間的此在的時間性,像“鐘錶”這樣的東西也已一道被揭示出來了,也就是說,一道揭示出了一種上手事物——在有所期備的當前化之際我們可以借其有規則的重復通達它的那樣一種上手事物。[P467]
無論如何,只有現在才可能充分地從結構上描述所操勞的時間:它是可定期的、伸張分段的、公共的、並且它作為具有這種結構的時間屬於世界本身的。[P468]世界時間比一切可能的客觀都“更客觀”,因為它作為世內存在者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向來已隨著世界的展開以綻出視野的方式“客觀化”了。[P473]
但世界時間也比一切可能的主體“更主觀”,因為若把操心的意義適當地領會為實際生存著的自身的存在,那就只有時間才一道使這種存在成為可能,時間既不在“主體”中也不在“客體”中現成存在,既不“內在”也不“外在”;時間比一切主觀性與客觀性“更早”“存在”,因為它表現為這個“更早”之所以可能的條件本身。[P473]時間與空間的問題似乎至今仍然是哲學與科學的一大問題。
“時間即是計算在早先與晚後的視野上照面的運動時所得之數。”亞裏士多德是從生存論存在論的視野上反得這一定義的。[P475]對於流俗的時間領會來說時間就顯現為一系列始終“現成在手的”、一面逝去一面來臨的現在。時間被領會為前後相續,被領會為現在之“流”,或“時間長河”。[P476]
儘管在柏拉圖的眼界裏時間原是不斷生滅的現在序列,他卻也不得不把時間稱為永恒的摹像:“但他決定製造一種關於永恒的運動著的影像;在當他要安排好天空的同時,製造了一種永恒的影像;這種影像按照數學運動。這是持駐于一的那一永恒的影像。我們所說的時間這個名稱正是給與這一影像的。” [P478]
把時間當作一種無終的、逝去著的、不可逆轉的現在序列,這種流俗的時間描述源自沉淪著的此在的時間性。流俗的時間表像有其自然權利。它屬於此在的日常存在方式,屬於首先佔據統治地位的存在領會。從而,歷史也首先與通常被公共地領會為時間內的演歷。[P481]
綻出視野的時間性首要地從將來到時。而流俗時間領會則在現在中看到基本的時間現象,而這個現在是從其全體結構切開的純現在,人們稱之為“當前”。[P482]亞裏士多德說:“但如果說除了心靈與心靈之意念外就沒有任何東西自然地有計數稟賦,那麼,如果沒有心靈,時間就是不可能的。”又有奧古斯丁寫道:“所以,在我看來,時間無非是一種廣延;但我不知它是何種事物的廣延。而它若不是心靈自身的廣延,那倒是令人驚異了。” [P482]
歷史本質上是精神的歷史;這一歷史在“時間中”演進。所以“歷史的實現落入時間之中”。[P483]空間即是時間,亦即,時間是空間的“真理”。[P484]空間是點之複合的無區別的相互外在。……是“點之可能成為點。”否定之否定作為點之所以成為點即是時間。……點之所以何能自為建立自己的條件是現在。[P486]“現在”恰好就在點的自為建立自己之際浮現出來。
作為對亞裏士多德傳統時間觀念的繼承,黑格爾的命題是:空間“是”時間;柏格森卻倒過來說:時間是空間。[P488]精神在其實現過程中落入被規定為否定之否定的時間之中。……黑格爾的精神的本質是概念……概念就是自身以理解著自己的方式得到概念理解的情況。……“我是純粹概念自身,這概念作為來到了此在的概念而存在。” [P489]
精神發展的標的是“達到它本己的概念。”發展本身是“針對自己本身的艱巨而無止境的鬥爭。”把自己帶向其概念的精神的發展是不安的,這種不安即是否定之否定;所以,落入“時間”這一直接的否定之否定適合於自我實現著的精神。[P490]精神與時間都具有否定之否定的形式結構,黑格爾借回溯到這種形式結構的自一性來顯示精神“在時間中”的歷史實現的可能性。精神與時間被委棄于形式存在論的和形式確證的最空洞的抽象。[P491]“精神”不落入時間,而是:實際生存作為沉淪的生存,從源始而本真的時間性“淪落”。[P492]
從此在的根據處出發,從生存論存在論上著眼于本真生存活動與非本真生存活動的可能性來闡釋實際此在的源始整體。時間性公開自己為這一根據從而為操心的存在意義。[P492]
哲學是普遍的現象學存在論,它是從此在的詮釋學出發的,而此在的詮釋學作為生存的分析工作則把一切哲學發問的主導線索的端點固定在這種發問所從之出且所向之歸的地方上了。[P493]
研究一般存在“觀念”的源頭與可能性,借助形式邏輯的抽像是不行的,……像“存在”這樣的東西是在存在之領會中展開的,而領會之為領會屬於生存著的此在。……此在的整體性的生存論存在論建構根據於時間性,因此,必定是綻出的時間性本身的一種源始到時方式使對一般存在的綻出的籌劃成為可能。[P494]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就此打住結束了他的精緻而華麗的演出。但是這似乎必然是沒有結果的結果,不是他寫不下去或者不想寫,關於“存在”的問題向來就是這樣神秘而源始地令人水霧一頭,存在以存在與非存在的不斷轉換的漩渦式的存在而存在著,神性止步,緘默無語。
【十一】
中國有所謂“我注六經”和“六經注我”的說法,這代表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治學態度和方法。
我想最好的注解方法,詮釋(闡釋)方法,如果意在遵循作者的原意,那麼莫過於讓作者自己說話,特別是讓作者用他自己的口吻、語匯、心靈、心理來展開他的言說,這就是為什麼劍門若郎在解讀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存在論哲學時大膽大段大段地引用海德格爾的原文以及通過海德格爾的語匯及其核心思想來嚴密而又跳躍性地勾連出海德格爾的思想圖景的道理了。
劍門若郎讀書筆記式的勾連出海德格爾思想圖景,意在批判性地還原其思想,推出其優秀面,同時揭示其不足之處。通過耐心地解讀,我們發現,海德格爾主要有這些風格特點:首先,海德格爾是一個非常獨斷而自信的人,他發明和更新了不少語匯,形成了海德格爾式的語言,存在主義式的語言,可以說海德格爾的語言特點給他自己營造了一個獨特的世界,不僅如此,其思維也是非常獨特的,往往敢於掘進和大膽懷疑,充滿了頗具個性的獨斷和自信,也是包蘊著某種激情的冷峻風格;其次,海德格爾非常具有耐心,有意無意地借助其淵博豐富的語言學知識似乎玩起了精緻而華麗的語言遊戲,一方面,他在某些領域掘進地非常獨特和深刻,哪怕是錯誤的道路,就算是迷誤,似乎也要作成偉大的迷霧,另一方面,他那看似較真的語言學態度及其看似嚴謹決斷的思維道路往往不是很好地解決了問題,而是往往把簡單的問題倒是弄得硝煙瀰漫、令人水霧一頭,莫可名狀,亦即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了;再其次,海德格爾野心勃勃,他似乎很有尼采的精神內涵,只不過其表現方式大不同於尼采,尼采是以預言先知式的高調反叛傳統,大聲疾呼,重估一切價值,而海德格爾也是批判和否定傳統的,他認為傳統思想文化代表的是對存在的遮蔽,是精神文化的迷霧和沉淪,而他海德格爾則要重新審視這被遮蔽了數千年的存在道路,拯救存在之沉淪,探尋存在的真理意義,相對於尼采的道路,海德格爾似乎是較為克制地理性探尋的道路,當然其內涵也是激情而深刻的,一種包蘊激情的冷峻風格;最後,雖然海德格爾情思宏大,野心勃勃,用心良苦,但是他的宏大情思似乎未能真正得以成功實現,他許諾的太多,而人們能夠收穫的東西卻是有限的,甚至他的情思最終是半途而廢的,雖然他的影響是較大而深遠的,但是他的學說與其說提供給讀者的是真理性的思想文化,倒不如說他更多的是提供了具有獨特語言蘊含的審美性的詩化了的哲學思想,亦即是說海德格爾的哲學代表的是“詩化哲學”或者說“哲學詩化”,劍門若郎認為這條道路恰好代表了哲學精神蘊含的衰敗和末路,在柏拉圖那裏,哲學和文藝曾經激烈地爭奪過精神文化的領導權,最終,哲學以它的豐碩成果及其宏大深遠的整體性內涵天然獲得了桂冠,成為了文化的精神領袖和存在的守護者,但是海德格爾的哲學的詩化是較為突出而嚴重的,有意無意的,似乎更是有意而為的傾向,這在他後期的哲學似乎變本加厲了,哲學於是喪失了它的整體構思能力及其宏大而深遠的精神內涵,沉淪到詩意化了的文學世界,真正的哲學精神天然會斷然拒絕有意為之的審美化的文學道路,神龍豈可嬗變為鳳凰呢?
劍門若郎認為,真正了不起的哲學天然就是偉大的詩篇,但是反過來說卻不能成立,再偉大的詩篇它也絕不是真正的哲學。這是哲學和文學的本性決定了的某種存在關係。偉大的哲學家往往是一個戰士和詩人的雙重內涵。柏拉圖推崇哲學而流放詩人,但是他卻創造了了不起的哲學詩篇,他的哲學就是偉大詩篇。尼采也同樣創造了了不起的偉大哲學詩篇,尼采甚至高揚文藝的優越地位,自覺地把藝術上升到生存本體論的高度,尼采那裏已經出現了哲學的詩化或者說詩化的哲學,但是尼采的哲學精神內涵卻是根本主要的。然而,海德格爾這裡,我們感到的卻是逼人的詩化了的哲學,哲學的審美化正是哲學的根本衰敗。
由此,海德格爾作為哲學家他提供的真理性的東西少,然而作為詩人,他卻帶給世人莫大的欣慰,因為其賦有獨特思想蘊含的詩意。這就是為什麼我劍門若郎曾推崇老子的哲學,渾厚質樸,大氣智慧,而莊子的哲學就差了很多,因為莊子那裏哲學詩化得比較明顯,所以,作為一個詩人來看,莊子的文學影響倒是古今少有的,但是作為哲學家來說,莊子則遠遠不如老子的深厚了,雖然莊子自詡雄視百代,他推崇老子而自認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此言差矣。
回過頭來看,海德格爾的哲學代表西方文化已經沒有能力構建整體性的宏大而深遠的哲學了,他的哲學更像是以心理學為內蘊的各種哲學思想甚至語言學的融匯,已經喪失了尼采那樣作為傳統哲學的最後一人和開天闢地的哲學的第一人的偉大性了。尼采的了不起主要在於他以奇高的天性和勇氣審視和重估了人類文化的一切精神價值,他的視野是整個歐洲乃至人類的,他的使命就是要拯救存在,他是通過教育沉淪中的現代人要知道什麼是優秀和高貴來試圖實現他的歷史使命的,因為他難以忍受越來越女性化的人類文明,這就是他為什麼要呼喚“超人”了。尼采的價值主要是他大大解放了人們的精神。故而,有人將他和柏拉圖並列,甚至說西方哲學好比是一座巨大的橋梁,如果說柏拉圖是第一個橋墩的話,而尼采正是第二個橋墩。筆者是讚賞這樣的眼光的。
海德格爾有尼采的某些精神蘊含,也有自己獨特的精神風貌,于西方現當代思想文化來講,算是一個較有影響的大哲學家,他幾乎是作為存在主義的奠基者和大師而倍受世人關注和推崇的,其實,他的影響似乎主要體現在文學領域,由此可見我前面的批判是很有道理的了。
最後,我要略作說明的是此文主要根據的是海德格爾的代表作《存在與時間》的中文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二零零六年三聯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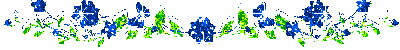
 薩克斯風-唯有你
薩克斯風-唯有你